徐浩新、陈家明两位教授,分别辞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美国杜克大学免疫系终身教授兼系副主任的职务,回国全职加盟良渚实验室。
在实验室园区崭新的科研楼里,记者见到了这两位海归科学家。
两位教授有着“漂亮”的履历,都曾担任国际上学术水平最高的会议之一——高登会议(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的分会主席;在《Nature》《Science》等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大量高水平论文,援引次数高达两万多次。溶酶体和离子通道、细胞死亡和免疫学分别是徐浩新、陈家明的研究领域,虽然不被大多数人熟知,但是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肿瘤、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治疗,许多医学突破都仰赖他们在基础研究旷野里每一次微小的前进。
访谈中,两位学者的回答真诚而务实,他们很少提及往日光辉,坦言自己的顾虑,也对未来满怀憧憬。他们告诉记者:“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推动着它前进,我们不想做大洋彼岸的旁观者。”

徐浩新在良渚实验室

陈家明在良渚实验室
这里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记者:两位教授是什么时候开始酝酿回国的计划,为什么归国?
徐浩新:我对浙大还是比较熟悉的,与学校里研究离子通道的同行们经常交流,这几年也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回国。
去年3月,我提前回国,就想了解国内实验室的情况,这对于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在那个月里我看到了国家科研环境的大变化,国内实验室的人员配备、设备方面的条件也给了我信心。
陈家明:回国是我一直都有的打算。我在香港读完中学就去美国了,当时没有想过会在那里待那么长时间,只想读完本科回来当个老师。我的求学经历中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也希望自己能够为祖国培育下一代的青年。
当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身边的朋友意见不一,许多人鼓励我回去,也有人会问我“你是认真的吗,想清楚了吗”,我没有在内地上过学,没有工作经验,没有资源和人脉,这确实是个有些“疯狂”的决定。
但是我们在人生里做每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都有冒险的成分,可能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输得起”。我其实挺幸运的,目前在美国想要做的工作完成得差不多了,国内的科研实力发展很快,也很需要更进一步的攻坚,我想接下来应该做一些真正想做的事。
记者:二位刚刚都提到国内科研环境的改变是一种吸引力,那么你们回国之后看到了哪些变化,有怎样的感受?
徐浩新:我觉得变化是巨大的。20多年前我出国的时候能明显感受到国内外的差距,那时国外研究所里高端的设备、仪器都让我觉得新奇。
后来每隔几年我都会回国,每次都能看到科研环境在一步步变好。做生物实验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现在我们所处的这栋楼里就装置了先进的恒温系统,实验室里的设备都是崭新的,硬件条件有很大的提升,我们也获得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原本在国外才能实现的科研抱负,现在在“家门口”也有条件实现。
陈家明:中国发展的速度超出我的想象。
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科技经费投入大幅增加,我们申请科研基金的流程更快,也更充裕。最关键的是,科研机构之间有了各种更密切、更灵活的合作方式,有利于推动临床转化。
浙大一院总部一期与实验室靠一座廊桥相连,走上几步,就能和医生们交流,他们观察到的临床情况也给我们带来了研究的新思路和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也体会到传说中的“内卷”,能够明显感觉到国内“卷起来”的科研状态,我们良渚实验室有很多海归青年教师,在这个时代,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同时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记者:二位在回国的时候都接到了不同学校发来的“offer”,为什么最后都选择浙江大学,落地良渚实验室?
徐浩新:选择浙大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自己是浙江人,家里人也希望我回离老家近的单位工作。
还有一点是我能感受到浙江对科研人才的重视,各级部门时常联系我们,了解我们在科研中的实际需求。
良渚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的研发机构,除了日常做实验的科学研发、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创新基金和团队培养方面的工作也能在这里同步开展,这样灵活的运作机制是一块充满活力的土壤,相信我的理想在这里能够开花结果。
陈家明:我从小在香港长大,但是我的父亲是舟山人,母亲是绍兴人,他们时常和我讲起家乡。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回老家金塘岛;中学放暑假的时候,我来内地“背包旅行”,北京、西安、成都、兰州、银川……走过的地方越多,归属感就越强烈。
父母的乡情非常浓厚。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很深。2017年,我陪父亲回舟山,和他一起坐公交车,他喜欢听车上广播一站一站报出地名。我陪他一起听着,和乡邻聊聊家常,牵引出很多的回忆。父亲去世前给我打过电话,希望我能回来给家乡做贡献,这也坚定了我的选择。
当时与很多所学校接洽,与浙江大学的几位老师接触了两年多,我能感受到他们的诚意,大家都真正想要做好教育和科研,想要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做点事。
我非常欣赏他们,原先我还担心在国内没什么熟人,现在这里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朝着一致的目标前进,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其他方面如果有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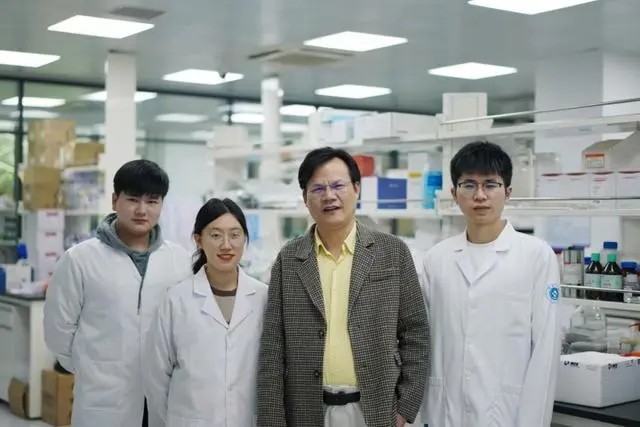
徐浩新和研究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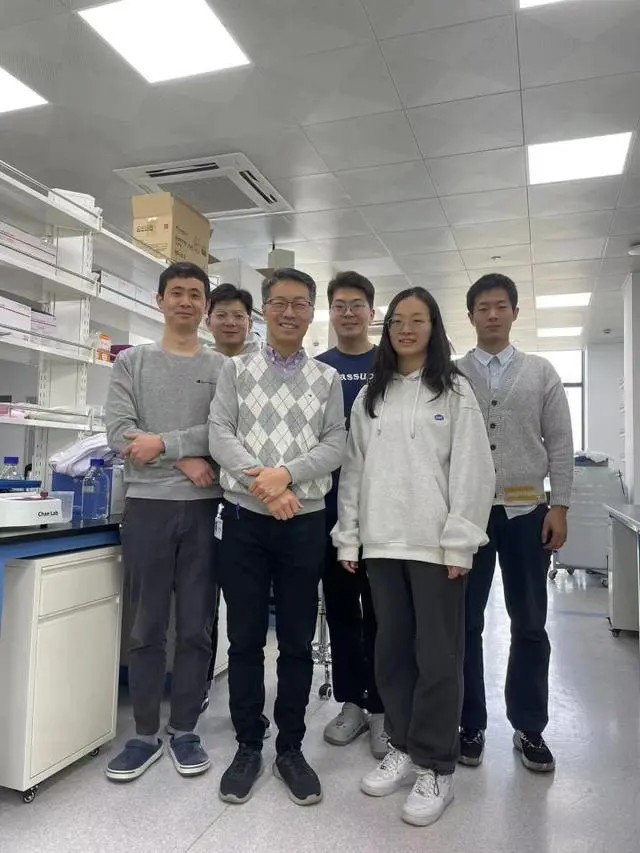
陈家明和研究团队
“走向治疗”是团队的一致期待
记者:两位教授都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在各自的领域有世界顶尖的成果产出,能和我们介绍下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进展吗?
徐浩新:我的研究方向是溶酶体和离子通道,和陈教授的研究领域也有关联,通俗地讲,我们关注细胞垃圾的“处理和降解”。
由于遗传、环境、年龄等因素,细胞垃圾会开始囤积,这些垃圾都是由细胞的“垃圾处理中心”——溶酶体来解决的,而离子通道是调节溶酶体功能的重要切入点。
如果这个“垃圾处理中心”运转失常,垃圾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后果很严重。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疾病、肿瘤、衰老等都与溶酶体的功能异常密切相关。比如阿尔兹海默症的病因主要是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聚集沉淀,阻碍细胞尤其是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
怎样才能增强细胞垃圾的处理效率?我们的研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探讨用什么样的化合物分子提高溶酶体的功能。2008年,我的团队率先创立了细胞内的一种细胞器——溶酶体上进行离子通道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突破了溶酶体离子通道研究的瓶颈。
陈家明:我的研究领域是细胞死亡和免疫学。和人的生命进程一样,细胞也在扩增,也会衰老、死去。就像随地扔垃圾会引起环境问题一样,细胞死亡后产生的垃圾可能导致体内环境异常,促进炎症的发生。
细胞死亡是调节免疫功能和炎症的重要机制,人类90%以上的疾病都和炎症有关。我们团队一直在做的就是研究细胞死亡和炎症的关系。
我们发现细胞死亡并非都是意外的,死亡有很多种类型,我们主要阐述炎性细胞死亡——细胞坏死性凋亡的机理,这是一种为维持内环境稳定,由基因控制的细胞自主有序的死亡。
2009年,我们终于找到了调节这类死亡的关键分子,确定了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3(RIPK3)作为坏死性凋亡的调节因子,这个成果开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新方向。
记者:对于之后在良渚实验室开展的研究,两位有什么计划和想象?
徐浩新:“走向治疗”是我们实验室团队的一致期待。
在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中,有近15%与离子通道相关,我们希望上游的基础研究成果能够成功转化,应用于疾病治疗。
到目前为止,我们鉴定了12种未知离子通道蛋白,包括8个溶酶体离子通道蛋白。之后我们会继续开展溶酶体离子通道的相关研究工作,同时也将目光拓展到其它细胞器上;另一方面我们将在已发现的7个离子通道上展开转化研究,用于临床治疗。
我们的目标是,这些离子通道都能开发出相应的药物,治疗那些困扰人类已久的疑难病症。比如我们之前在Cell(《细胞》)发表论文,证明了TMEM175(溶酶体膜上的氢离子通道)是一个帕金森病的重要遗传风险因子,由此开发出相应的小分子激动剂并开展了相应的临床前实验。
陈家明:团队在研究病毒干扰免疫功能背后的机理,我们在寻找究竟有没有方法能够通过调控细胞死亡、调控身体里炎症反应的力度,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更有效地对抗流感、新冠、肿瘤等疾病。
我们想找到一些病毒的基因来干扰细胞的坏死性凋亡,所谓“以毒攻毒”。不久前,我们团队就从牛痘病毒中筛选可以调节免疫应答的病毒分子,期待未来能够制作出针对包括流感、新冠和肿瘤的更安全、有效的疫苗。
用“有品位的科研”引导科技向善
记者:两位教授都提到想用自己的国际化背景为浙江的科技创新做点什么,对于浙江在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攻关,你们有什么建议?
徐浩新:评价体系的改变对于科研创新很重要。
科研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没有绝对的失败。我们不能完全按完成生产任务、产出产品的方式,去评价科研人员。就像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溶酶体离子通道的研究,这类基础研究可能很长时间都等不到结果,而有些人会急切地问“成果怎么还不转化”“研究到底有什么用”,我们希望能够改变大家对于基础研究工作的认识,改变短期的、纯量化的评价方式。
我们期待的评价体系,以创新能力和成果质量为标准,参考国际同行的评价。结合不同的学科特点,形成一种长周期的评估机制,同时强调“有品位的科研”,考量科技背后的价值观,引导科技向善。
在这点上,高校、社会要给优秀人才充分的信任、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要在顶层设计和组织层面上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陈家明:目前来看我们研究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科研以外的其他事物上,许多年轻同行反映“静不下心来”做研究。
对于大部分科学家来说,创造力最强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研究的10年,这是一段很关键的时期,希望能够给予青年研究者在时间上一定的保护。
国外允许青年老师在第一年不承担教学任务,他们称为“protected time”(受保护的时间),国内有不一样的现实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力所能及帮助他们适当减压,少承担一些比较琐碎的任务型的工作,或许是一个能够激发更大创造力的办法。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刚开始研究的时候特别像进入了一个游乐园,机会很多,每个游戏项目都在向我们招手,眼花缭乱,可能很多青年老师都有这样的困惑。如果能够在前几年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去思考、去尝试究竟要走哪个方向,对于他们之后的研究生涯会更有帮助。
记者:对于青年研究者的培养,有哪些作为“过来人”的建议分享?
徐浩新:科学不能封闭,需要开放、交流和碰撞。
我一直重视学术交流。平时我会定期组织线上研讨会,研讨会上既有国际学术大咖主讲,也有很多国内青年科学家分享,至今已有30期,开放给良渚实验室和浙江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今年4月,我们将在西湖边举行第一届中国溶酶体生物学大会,这个研究领域比较小众,所以想给同行们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也想让学生们也有机会接触前辈、学习经验。
作为归国科研工作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去推动国际合作。希望通过这些研讨会、交流会,架起青年学者与世界沟通合作的桥梁,助力他们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陈家明:回国后我一直思考怎么培养青年人才,带好这个团队。我发现这里的学生大都比较含蓄。确实,尊师重道、谦虚,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优点,这和西方人的文化很不一样,但有时候我们不敢挑战和质疑权威。
我常常和学生说,不要觉得我是老师就一定是对的,我的观点不一定比你们的高明。培养容忍失败、大胆创新的科研氛围是很重要的,我鼓励他们提出见解、学会发问、敢于质疑,让团队里的人更有安全感。
科学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就是因为总有一群人在深入思考、挑战现状、开创未来。如果我的学生是这样的人,我会非常开心。
在外开研讨会的时候我都会把青年教师或学生带上,希望有我在身边,他们不会那么紧张。我也会用自身的人脉资源,帮他们引荐。其实很多青年研究者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但如果别人只看到他们在文章中的名字,却不识其人,就很难让人记住。相反,如果你跟那些人讲过话、握过手,他们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
新闻+
【徐浩新】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现任良渚实验室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徐教授是溶酶体离子通道和疾病研究的世界领军人物,组织并担任首届高登会议(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细胞器离子通道和转运蛋白分会议主席,国际药理学TRP通道分会主席。徐教授长期从事神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近几年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PECASE),密歇根大学杰出教授奖等奖项,发表高水平论文70多篇、H index 53、文章累计引用两万多次。
【陈家明】
本科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专业),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现任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良渚实验室特聘教授。陈教授作为细胞死亡和免疫学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他组织并担任高登会议(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细胞死亡分会会议主席,也是国际知名期刊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细胞死亡与分化》)的编委,共发表高水平论文80余篇,H index= 50,文章累计引用两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