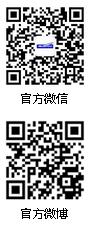三、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文明交往史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五个伊斯兰国家接壤,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三个伊斯兰国家隔海相望。中国周边的天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脉、喜马拉雅山和阿勒泰山见证了中国与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国家的文明交流互鉴,也见证了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兴衰。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第一次崛起是在汉朝,第二次崛起是在唐朝,第三次崛起是在元朝,第四次崛起是在清朝。每一次崛起都见证了中国和这个地区发生过的密切互动。
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流历史悠久。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有深度融合。从阿拉丁神灯时代到阿里巴巴网购时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一直有交流。相传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派门徒4人来华传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于唐贞观初年经海上丝绸之路在广州登陆,开始在中国传教。据传艾比•宛葛素和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于贞观元年(627年)捐资修建了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公元651年,前来中国的第一位阿拉伯使者奉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之命,到了长安,觐见唐高宗,介绍了大食帝国和伊斯兰教。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其发展初期的唐代,就有穆斯林努力学习和适应儒家文化。据《全唐文》卷767记载,唐宣宗时就有来华的穆斯林后裔李彦升考取进士。当时一名文人还写了一篇题为《华心》的文章,赞扬李彦升懂得中国礼仪,是一位“形夷而心华”的人(马明良,2009)。
穆罕默德的一句话“学问远在中国,亦应去求”对穆斯林的鼓励很大。自唐永徽二年(651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7年中,大食遣使交聘者,计有39次之多。自宋开宝七年(974年)至绍兴六年(1136年)的162年间大食遣使交聘者计有20次,可见大食对中国之重视。唐朝天宝十年,高仙芝征伐石国(塔什干)措置不当,在怛罗斯地方引发了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大食俘虏了一位名叫杜环的随军书记。杜环在大食住了 12年,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才由海道回到中国。他把这12年的见闻,写成了一部《经行记》,书中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书中还记录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礼拜、封斋和饮食:“(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哈里发)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这是中文第一次记录伊斯兰教(高文远,1988)。杜环在行记中,还有名有姓地记录了他在阿拉伯地区见到的中国商品和中国人:“绫絹机抒,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吕礼等。”
南宋有两本书记载了当时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一本书是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另一本是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这两本书写作时,宋已南渡,诸蕃惟市舶仅通,故所言皆海上丝绸之路事。但这两本书都对伊斯兰信仰和阿拉伯国家有生动的记载。《岭外代答》描述了当时麦加朝圣的盛况: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结甓成墙屋。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王,皆遣人持宝贝金银施舍,以锦绮盖其方丈。每年诸国前来,就方丈礼拜。并他国官豪,不拘万里,皆至瞻礼。方丈后有佛墓,日夜常见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过。”《诸蕃志》记述了大食国的伊斯兰信仰: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曰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月。每日五次礼天。”《诸蕃志》还报道了大食国穆斯林商人在泉州生活经商的事迹:有番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从上述引文看出,这两本书在用词上“伊斯兰教”与“佛教”不分,在描述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出生地时,不断出现“佛”字,如“有佛名麻霞勿”“佛麻霞勿出世之处”。
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是记述包括众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东西两洋的重要人文地理著作。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马欢读过《岛夷志略》,随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翻译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有一半内容来自《岛夷志略》。
2018年除夕夜,中央电视台在春晚向全世界首次展示中国收藏家几年前从日本重金购回的明代《丝路山水地图》(又称《蒙古山水地图》)。这幅长达30米的山水地图涵盖了从嘉峪关一直向西到麦加的广阔区域。郑和的后人郑自海(2018)认为《丝路山水地图》实为中国穆斯林传统的陆路朝觐路线图,其所述从嘉峪关到麦加的地理资料,也可能出自到麦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地图上出现最多的是阿拉伯长袍装束的人物形象,因为这个广大地区在15世纪中期已经基本伊斯兰化。画面中的人物或手牵胳驼,或背负行嚢,或骑马行走,或席地而坐,面前放着酒壶和酒杯;或在树荫之下乘凉;衣服则有红、白、绿、赭等色,有的地方还画有伊斯兰风格的野地帐篷,有人物出入其中。相关的文字材料则证明当时的中国人对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着相当透彻的了解。
从跨文化交流看,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皆是穿过东亚、南亚去往中东和欧洲之路。
为促进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明朝的郑和。伊斯兰教自唐传入中国后便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儒家文化在中国占统治地位。郑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虽是穆斯林,但是他“才负经纬,文通孔孟”(卢新宁,2005)。他在奉使西洋30年间,将儒家和伊斯兰两种文化集于一身,并在实践中进行有机的调和。他每次出使西洋都有涉及伊斯兰教的活动,均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学习。郑和被朱棣皇帝授予“钦差总兵太监”军衔,下西洋遍访沿线的伊斯兰国家。他的翻译是穆斯林马欢,马欢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著有《瀛涯胜览》。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外交通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甚至可以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媲美(新华网,2005)。《瀛涯胜览》记载了明宣德六年,内官太监洪保选差通事等七人前往麦加,并画天堂图回京。因为洪保是代表国家行为访问麦加,可视为中国政府组团的第一个穆斯林朝觐团(郑自海,2018)。马欢等7人还受郑和派遣到麦加朝觐,在完成朝觐功课的同时摹绘了《克尔白图》,带回国上奏朝廷。另一位随行者费信也是穆斯林,四次跟随郑和下西洋,著有《星槎揽胜》。再有一位穆斯林随行者是巩珍,他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三本书将伊斯兰国家的风土人情、风俗礼仪、山川地理、物产气候、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介绍到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人正确认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伊斯兰世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梁启超高度评价郑和下西洋,他写道,“成祖以雄才大略,乘高帝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派郑和扬威德于域外。成祖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梁启超,1905)。有学者提出,郑和航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除了访问少数佛教国家外,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他都访问过(陈炎,2005年)。
郑和在沿线国家还修建了清真寺。郑和所建清真寺对后来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一带清真寺建筑风格有一定的影响。从现存爪哇 15世纪的清真古寺来看,它们都具有多层屋顶、宝塔状的上层建筑(宣礼楼等)。但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信仰上的极端主义,更不是抱有“普世价值”,到世界各地推销某种“先进文明”的布道士。郑和本人出身回族世家,他一身兼信伊斯兰教和佛教两种宗教,受过菩萨戒(宫慧如,2005)。明成祖除了派遣郑和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下西洋外,还派遣陈诚等外交官五次出使西域,最远到达帖木儿帝国的名城哈列(今阿富汗的赫拉特)。陈诚回国后写了《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两部纪实性报告,呈送给朝廷。通过这两本书可了解明朝时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各国的状况,及这个地区与明朝的外交关系。清朝马德新用八年的旅行(1841年至 1849年)赴麦加朝觐,所著《朝觐途记》详细记载了取道海上丝绸之路赴麦加朝觐的路线图。《朝觐途记》记述了阿拉伯和西亚的一些文物古迹、史地沿革、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是研究清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重要文献(马丽蓉,2013)。
伊斯兰教经陆海两路传入中国,因伊斯兰教不主动向外传教,而主要靠先知穆罕默德的弟子或后裔等特殊信奉者自身的繁衍生息发展。这个漫长的传入中国过程中,伊斯兰教既不攻击其他宗教,也不诋毁儒家,赢得底层民众好感和认同(马丽蓉,2013)。来中国开展贸易交往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和中国人融合,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回族。这种融合不仅是来自中亚的阿拉伯人等与中国人的民族融合,它还导致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化的交融互鉴。
早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不仅采用了儒家的观点,还创造了“儒家化的伊斯兰教”。清初,中国特色经学家——伊斯兰儒家化的哲学思想家刘智不仅研习伊斯兰教经籍,还博览儒释道典籍,对各种学术思想都有深刻并全面的认识。刘智一生著作丰富,其著作被尊为“汉克塔布?(Han Kkab,又译为回儒汉典,即用儒家语言表述的伊斯兰著作)。回儒把《古兰经》翻译为汉字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阿拉伯语一共只有26个字母,构成整个语言文字。相反,中文有超过50000个汉字。因此,使用儒家和道家的词汇、术语和概念,使用象形文字翻译《古兰经》,需要付出惊人的努力,这一任务是一代人完成不了的。刘智所著的《天方典礼》被收入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刘智对于中国穆斯林最为集中的西北地区影响深远,被后世赞誉为“大伊玛目”。研究中国伊斯兰历史的学者詹姆斯•弗兰克尔写道:汉克塔布旨在使用儒家——中国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伦理和哲学流派之的语言,向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教授有关伊
斯兰的知识。在汉克塔布背后的中国穆斯林学者认为自己‘同时是中国人和穆斯林'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能够把伊斯兰和儒学的宗教与哲学概念无缝对接。”(Ang,2015;转引自Frankel,2009)
最早向西方(在古代,相对于中国,阿拉伯世界也是西方)介绍中国的外国人,不是公元13世纪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而是公元851年一位名叫苏莱曼的阿拉伯人。他的著作《苏莱曼东游记》是阿拉伯人第一次用阿拉伯文记载在中国的见闻,记叙了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书中还提到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在中国受到尊重。
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演讲中,不仅提到了郑和,还提到了 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新华网, 2014)。伊本•白图泰在其著作《伊本•白图泰游记》报告了他在泉州、广州、鄱阳、杭州和北京等地的游历。迄今所知的唯一一部有关中国的波斯文古籍是16世纪阿里•阿克巴尔写的《中国纪行》,这本书介绍了他在明朝时游历中国见到的社会的方方面面。